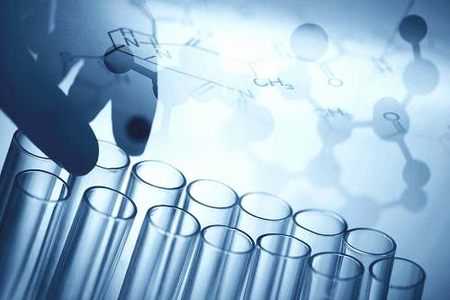风大富说:
多年前看了刘庆邦的神木爱上文学。对他的作品有不一样的感情。他讲故事都是一点一点的交待,不像公号惯常的直白。慢慢看,内容有嚼头,写黄处也写得真实,没有淫秽感。
老婆不让雄上身已不是三日五日,雄有些饿,但雄不打算来硬的。强摘的瓜不甜,这俗话的意思他懂。
雄下了班,走过一段充满陈尿味、煤巷般漆黑的楼道,摸回那间小屋。屋里冷锅冷灶,地上半盆恶水,案角一只脏碗。一匹老毛耗子在窗台啃那块干缩的肥皂,边啃边吐,把肥皂嚼得如一堆绞碎的肉馅。见有人进来,它从容地抹抹嘴巴,一跃遁到床下去了。老婆侧身在床上睡,枕边一窝子头发。老婆的头发很好,又粗又硬。
雄脸上苦了苦,到床前问老婆吃饭了没有,想吃什么。老婆不吭,他就隔着被子触触老婆的肩膀头。老婆胳膊一抡,身子平过来。老婆胳膊抡得大了些,从被窝里露了出来。老婆的胳膊匀溜,光洁。雄眼前一亮。这只胳膊和另一只胳膊合成一股,缠过雄的脖颈,缠过雄的腰背,把雄的身体无处不缠到,让雄颠狂得喘不过气来,如今这不错的东西他只能看看了。他让老婆把胳膊盖好,免得冻着,欲借机把胳膊捏了,送回被窝里去。还没等人捏到,老婆像是料到有人要动她的胳膊似的,攥成拳头在床边擂了一下。老婆不但没有把胳膊收回去,还蹬了两蹬,把一条腿子从被下伸展出来。这下更不得了。他家的床单长时间不洗,已有些发黑。在这发黑的底色衬托下,脱被而出的腿子圆润,精白,放着光华。腿子上下散发出一种热烘烘的诱人气息,推都推不开。略显肮脏的卧具也让雄觉得合适,可以放开手脚折腾。他把腿子至下而上瞅了瞅,心跳有些快,喉咙有些噎。以往两条腿子在他手上颠来倒去,从中得到的种种妙处如在眼前,似乎一伸手就可以重新温习。他不大持得住,身子不由自主地俯下去。
老婆一脚就把他踹开了。他后退了几步,差点蹲坐在恶水盆上。
原来老婆故意馋他。
“你……别当我不知道你的事儿,我掐死你!”
老婆坐起来,“掐吧,不掐死我,你不是人操的!”
雄把牙咬住,双手提在胸前扣成一个环,看样子要掐了。但他的手稍稍有些抖,抖着抖着双手扣成的环就散开了,双手死鸡翅子一样垂落下来。
“哼,借给你一个胆儿……”
雄往地上一蹲,哭了。他哭得哼哼叽叽,有点造作,“我哪点对不起你……你说……我哪点儿对不起你……”
老婆没说哪儿对不起她,她扯巴扯巴穿上衣服,头脸收拾了几把,就出门去了。
雄不哭了,追出来拦在老婆前头,说是跟老婆商量点事儿,要老婆回到屋里去,一切都好商量。
老婆说:“滚!”
雄说:“你小点儿声好不好……”他问老婆到哪里去,求老婆千万别到狗肉铺子里去了。
老婆说:“我的胳膊我的腿,想去哪儿去哪儿,你管不着!”
有的矿工和家属听见动静,开了门往楼道里探头。哪家开门,门口的楼道就放进一方子亮光。
雄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夫妻不和,遂换了和颜,对老婆的背影嘱咐说:“少给我打点酒,我喝不完。“
老婆头也不回:“你喝尿去吧!”
雄面子上下不来,就拧着头,做出恶狠狠的样子,一指老婆离去的方向:“行,你不听话,行……”
第二天下井,工友们问雄昨晚“吃了几口”。雄对这个问题像是有些挠头,又像是故意卖一个关子,笑了笑,不马上作答,反问人家“什么吃几口”。
问话的工友说:“被窝里的老婆碗里的肉,想吃几口吃几口。”
这是雄以前挂在嘴上的话,如今被人接过去提醒打趣,装糊涂是不行了。他脸上有些讪,说:“那当然……这事儿,操,还用说吗?!”
好几个工友往上架秧子,意思让雄还是说一说好些。
雄知道同行们爱听这个,如班后的几口小酒儿,用了才提神儿,他不能扫了弟兄们的兴。他说其实没啥意思,都是老一套,就是把昨日的事儿改造了一下,夸老婆的两条腿好生厉害,他刚走到床前,以为老婆还没睡醒,不料老婆动腿不动口,一下子就把他套进“辕子”里去了,挣都挣不脱,没办法,只好把“辕子”架起来“开走”。
有人问他“走”了多长时间。
他说,不长,大概一个多钟头吧。
一个工友夸他真不简单。他正要自谦一下,说马马虎虎,别的人都笑了。
大满说:“狗屁!”他问雄知不知道“丢人”两个字怎么写。
班长也笑着说:“今天工作面不用放炮了。”言外之意,经雄一吹,煤墙就塌下来了。雄从两个人话里听出,他和老婆的事儿人家已经知道了,有些蔫头,但鸭子倒了嘴还很硬,说反正他是实事求是,不信拉倒。
大满说:“铺一件破雨衣,睡在老婆床前冰凉地上的是谁!狗?”
那个夸雄“不简单”的工友,也学了雄的腔调,哭哭叽叽对大满说:“我哪点儿对不起你……我说不让你到狗肉铺子里去……你大面儿上让我过去好不好……”
雄有些恼,骂了一句娘,说以后谁再去他家蹲墙根子听房,他就跟谁拼命。
大伙儿觉得有些好笑,这雄,面子是命,命是狗卵子,该拼命的地方,他把命把儿攥着,不该拼命的地方,他倒来了劲。工友们对他不大客气,知他耳孔是圆的,却说了不少四棱子八角的话:
“手的名字叫巴掌,你懂吗?”
“他那点刚性早叫狗嚼吃了。”
“要是我,一刀子下去,不把他三年的陈粪放出来才怪!”
也有人会说笑话:“你们不理解雄,雄是发扬风格。”
……
雄没有再做声,刚才那个工友说的放陈粪的话似乎对了他的思路,他设想,一刀捅在秤锤腹部,再横着豁一下,秤锤的肠子肚子就流出来了。
一直没说话的是放炮工木,木靠煤壁半躺着,摘下的矿灯熄了,胶壳帽半扣在脸上,看样子像是对雄和他老婆四真的事儿漠不关心。木也是矿上的劳模,当初,四真不远千里来矿上坚决要求嫁给矿工时,矿上的头头选的是木,还把照片给四真看过, 据说四真是点过头的。木何尝不想要老婆,但他觉得整天讲黄段子的雄比他更需要女人,于是“让贤”了。最后“矿领导听取各方面意见,经过慎重研究”,才选定了脾气比较随和的雄。当然,据说四真对雄更满意一些。矿上为他们举行了排场很大的婚礼,两人的照片登在报纸上,四真的脸紧贴雄的肩膀,好多人都看到了。后来,四真和雄不知为何弄掰了,屠狗的秤锤插了进去。木不止一次看见四真在屠宰场里帮秤锤干活。秤锤牙上叼着刀,两手血糊淋啦,还用脚面踢四真的腚瓜儿,把四真踢得浪声浪气,满眼找床。这一切木也从来没说过。
据说四真是点过头的。木何尝不想要老婆,但他觉得整天讲黄段子的雄比他更需要女人,于是“让贤”了。最后“矿领导听取各方面意见,经过慎重研究”,才选定了脾气比较随和的雄。当然,据说四真对雄更满意一些。矿上为他们举行了排场很大的婚礼,两人的照片登在报纸上,四真的脸紧贴雄的肩膀,好多人都看到了。后来,四真和雄不知为何弄掰了,屠狗的秤锤插了进去。木不止一次看见四真在屠宰场里帮秤锤干活。秤锤牙上叼着刀,两手血糊淋啦,还用脚面踢四真的腚瓜儿,把四真踢得浪声浪气,满眼找床。这一切木也从来没说过。
雄打听谁有尖刀,他要借来用一用。最好是钢口好的,刀面子上带血槽儿的那种。
没人搭理他,巷道里一时显得有些静。
木一挺身子站起来走了,到工作面给炮眼装药去了。木装药是老练的,他做的炮响声并不宏大,甚至有点闷,但肚里开花,落煤的效果总是很好。
别人也三三两两走了。
雄对没人答应借给他刀子用颇为不满,认为别人是怕担干系。
这天下班,雄没有直接回家,到矿区的商业街去了。秤锤的狗肉铺子就在这条街上。太阳归西,天气干冷。一阵北风刮来,街面上煤尘飞扬。但一街两行生意仍很红火,水果摊儿、百货亭、服装间、理发店等,明灯高挂,如同白昼。门口遮一块黑帘子的放像室,不断传出噼噼啪啪的击打声和“嗨呀”的嘶叫声。室内大概人人都在抽烟,门梁上方的烟雾像烧锅一样滚滚而冒。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王无,披一床脏污的被子,还在街心坐着,有拉煤的汽车开过来,司机给他两三毛钱,他裹紧被子一滚,滚到马路边上,路就让开了。如果不给钱,他就抡起拐杖,把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。这里最多的是饭店和小酒馆。羊肉汤锅都支到饭店外头去了,红蓝火苗托着锅底,锅内白色的汤汁滚得疙疙瘩瘩。拉面的小伙子大张着膀子,把拉长的面像抖空竹一样抛上抛下。小酒馆年轻的女招待总是到马路中央去揽生意,只要有人走过,她们就笑眉笑眼,说:“天冷,喝点 酒吧!”被邀的人大模大样,毫不理睬,她们也不尴尬,仍笑眉笑眼,转向招徕下一个过路的人。
酒吧!”被邀的人大模大样,毫不理睬,她们也不尴尬,仍笑眉笑眼,转向招徕下一个过路的人。
雄听说酒能壮胆,本来打算用一点酒,可女招待过分的热情让他有点犹豫,据他的经验,别人对你太热情准不是好事儿。酒馆的老板娘隔窗看见他了,飞跑出来说:“大哥,我认识你,你可是好久没来喝酒了,还愣着干吗,快进去坐吧!”亲昵地从背后推了雄一把,还说:“做窑的谁不喝几口,不喝酒能算个男人吗!”雄见老板娘高个子,臀部肥大,嗓音粗得像个男人,就随她进了馆子。雄在窑下听说,差不多每个小酒馆里都有娼妇,上次公安方面来抓娼,其中外号“叫铺”的小娼妇一人就咬出嫖客一百多位,把矿上的头头脑脑都包括了。雄虽然不大相信这话,但他还是有些好奇,想判断一下女招待和老板娘哪个更像娼妇。他想,如果老板娘来行娼,凭她那骒马一样后座子,恐怕十条八条汉子都不在话下。
说话间酒、菜已上来了。老板娘夸雄是矿上的人尖子。雄问她此话怎讲。老板娘说:“天上掉下个花大姐,矿长点来点去点到你名下,要不是人尖子,几千口子壮丁,哪就轮到你了。”
雄没有接话,把酒喝下一杯。
老板娘问雄给“花大姐”种上没有。
雄说差不多了。
老板娘问差多少。
雄笑。
老板娘耳听八方,对雄和老婆的事是摸底的,她说:“你不用笑,我是向着你,才跟你说这些话,外面来的人都是没尾巴鸡,能飞来,也能飞去,你给她种上了,她身子一沉,兴许能实打实跟你过;一天不种上,她就一天人贱脚轻。我这话没说重吧?”
雄说老板娘怪有经验。
老板娘说经验不能白传授,让雄加个菜,多喝两杯。
雄不觉喝得嘴唇有点厚,头有些大,他说:“我要杀人!”这话在他耳边轰鸣了一下,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,可他看了看,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反应,这是怎么回事?
出了小酒馆,他记不清狗肉铺子在哪个方向了,就沿街乱走。既然去找狗肉铺子的屠户算账,不带家伙是不行的,他就去抠墙角的砖,抠不下,又去吭吭哧哧拔路边的粗树,仰脸发现是树时,他摇了摇头,“操,你……是不是喝多了,破坏绿化要罚钱的……”
后来雄见好几个人扒着一处铁栅栏门往里瞅,以为有什么稀罕,也飘着腿过去了。原来一个毛胡子、戴大金镏子的年轻人在里面逗狗玩儿。各色成年狗有七八只,挨挨挤挤蹲在一个墙角,前腿支地,身子直立着,眼睛很恭顺地望着毛胡子,像一堂学生望着老师。毛胡子说:“谁敢咬我,我给谁好吃的。”瞥一眼放在案子一角的两个猪肉馅饼和一根带肉的骨头棒子,走过去,把拳头在狗们嘴前比划。结果没有一只狗敢咬他,狗的嘴巴都紧闭着,拳头比划到谁面前,谁就低下头,塌下眼,回避了。毛胡子有些生气,骂着“胆小鬼,杀才”,穿大皮鞋的脚在狗堆里乱踢一气。狗们被踢得乱了阵脚,小声哼哼着,身子乱转磨。可毛胡子刚停止惩罚,狗们很快蹲回自己的位置,前腿支地,身子直立着,眼睛很恭顺地望着毛胡子,像一堂学生望着老师。
栅栏外面的一位看客说:“操!”
雄也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。
毛胡子把一个馅饼扔在地上,“谁吃?谁吃我不揍谁!”
狗们大概都把地上的馅饼看到了,有几只狗禁不住伸出生津的舌头很快地把两个嘴角舔了一下。大多数狗声色不动,眼睛仍然望着毛胡子,仿佛在表白说:“我没看见馅饼,我不馋,我是好狗。”
有一只长相英俊的白狗,似乎比较能领会毛胡子的意图,试探着从狗堆里走出来了,又试探着把香气扑鼻的馅饼嗅了嗅,仿佛在试探一下毛胡子到底有几分诚意。
毛胡子说:“好!吃,吃。”
白狗刚把馅饼叼住,毛胡子一记钩拳,把白狗击得飞起来,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白狗一声没吭,从地上爬起来走回狗列里。往回走的时候,它的腿有些瘸。
别的狗眼神里好像有些幸灾乐祸。
毛胡子走过去,把白狗的脊背从上到下捋了两遍,而后揪住白狗的一只耳朵,把白狗揪至案前,取过另一个馅饼,扔在地上,让白狗吃。
这次白狗不大敢吃。
毛胡子使劲把狗头摁下去,让狗嘴放在馅饼上,不吃就不撒手。
白狗样子有点不大情愿,小嘴微咂,很斯文地吃起来。
其它众狗条件反射似的各自往面前的地上找,找不到什么,都眼巴巴地盯着那个不要脸的东西细嚼慢咽,像是故意折磨人的狗嘴,垂涎滴滴啦啦流得一塌糊涂。
雄打了一个酒嗝,他想,下一个节目毛胡子该教狗算算术了。
毛胡子拿出半瓶白酒,啃下瓶盖,自己先喝了两口,而后把瓶颈放白狗嘴里,一直捣进狗的喉咙,将瓶子连同狗嘴往上一掀,掀得瓶底朝天,瓶内的液体泛着细碎的白沫一滴不剩地灌进狗肚里去了。
白狗伸伸脖子,讨好似的舔舔毛胡子的手,退着身子,挤进毛胡子怀里蹲坐着,面向它的那些同类。
那些同类简直有些愤怒了。
可是,白狗簌簌地抖起来,越抖越大。
这时,毛胡子把白狗提起,放倒在案边,单腿跪压,从案檐下的抽屉里抽出一把长苗子尖刀,穿针一样,从狗耳门刺进去了,刀苗子从下面透出好长。刀一抽出,略嫌粘稠的血浆子便注下来。
雄心上一惊,酒已醒了大半。这人是秤锤,他想。这个狗娘养的……他想大叫一声,或者狂暴地把铁门乱踹一气,可威没发成,不知怎的,他身上却禁不住抖起来。他两手抓着铁栅栏,带动得铁门也有些抖。旁边的人斜眼瞅瞅他,意思是:“又没宰你,你害怕什么!”
雄走了。雄没有忘记“算账”的事,可是他走了。他眼前还晃动着那些场面:利刃穿颅而过,白狗没有挣扎,只有眼睛大睁着,任冒着热气的鲜血流进一个脏污的盆子里;别的狗前腿大概已无力支撑身体,纷纷趴伏在地,眼神异常恐怖……雄觉得胃有些翻,脖子一挺,就“呕儿呕儿”地吐起来。他搜肠刮肚,吐得比较彻底,似乎连胆水都吐出来了。他犹嫌不够,换了一个地方,还直着脖子呕,他想把那颗没用的心疙瘩吐出来算了。
夜色朦胧中,雄看见一个人向这边走来,看样子像是他老婆。不用说这臭娘们儿又是去找秤锤的。他没有加以阻止,像是生怕老婆认出他是谁似的,赶紧到墙边向隅蹲着去了。他头埋得很低,如同寂寞的孩子欣赏蚂蚁搬家。估计老婆已错过去了,他才悄悄转过脸来,拿眼睛追踪一下。老婆把铁栅栏门踢了两脚,门就开了,老婆就进去了。
有人把雄的膀子拍了一下,雄不防,吓得一下蹲坐在地上。
原来是木。木问:“看什么呢?”
雄说:“没……没有呀。”
“怎么,喝酒了?”
“什么?喝酒?是喝了点……不喝酒能算个男人吗,是不是?”
木笑笑,把雄拉起来,轻轻拍拍他的背,说:“快回去休息吧,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雄很知趣,老婆不在家,他也不再到床上睡,他把那件胶面破雨衣铺展在床前地上,不脱衣服,盖件棉大衣,腿一蜷,就睡了。他想,人活着有啥意思,还不如死了。他鼻囊子有点酸。
老婆回来,手指上戴了一个金镏子,金镏子在灯下闪着亮光,雄一眼就看见了,一定是那个狗操的送给这骚货的。他打招呼说:“回来了,冷吗?”
老婆不理。
“洗脚吗?我去给你打点热水。”
老婆这次开了口:“去吧。”
雄一阵高兴,赶紧爬起来,拎起铁壶就出去了。
他打回满满一壶热水,刷净盆子,倒进半盆,用手试试水温,让老婆“洗吧”。
老婆没有洗脚,脱开了衣服,她把上身脱得露出了紧身毛衣,下身脱得赤精白条,腿一跨,蹲在水盆上了。老婆背向雄,雄把盆沿上那丰满的东西看到了,两眼发直,喉节一个劲往下走。老婆把一只手伸进水盆里,哗啦哗啦往上撩水,撩撩,轻轻拍两下。热乎乎的水蒸汽把一种刺激骨髓的气味散布得满屋都是,雄几乎喘不过气来,他问:“水……烫吗?”
老婆又不理他。
他很不成样子地笑着说帮老婆洗。
老婆眼立起来,“干吗?”
“就一次……最后一次……还不行吗?”
“半次也不行!”
“你说,你是不是我老婆?”
“问你自己。”
“我说你是我老婆。”
“你花多少钱娶的老婆?”
雄口有些噎,他把牙骨错了错,“你今天要是不让……我就不活了,我死,我自杀……反正活着也没劲。”
老婆说:“你死,你现在就死,看能吓着谁?!肉头!”老婆站起来,把裤子蹬上了。
雄很失望,也很委屈,他又哭了。这回哭得比较真实,边哭边抽自己的嘴巴子,“我叫你没本事……连老婆都管不住……你还有脸活着……我打你的脸……”
哭罢雄往地上一倒,就呼呼地睡去了。他睡得很沉。
雄突然醒过来时,一看表,正好是起床上班的时间,一点也不差。雄上班总是很准时。
木这天没有上班,他找到雄的老婆四真,说:“嫂子,我想跟你谈谈。”他脖子里的扣儿扣得紧紧的,衣服很整洁。他的表情也很严肃、沉静。他说雄这个人不错,能吃苦,守本分,心眼儿好,你要跟他好好过。他说雄弟兄们多,雄是老大,为了给弟弟们攒钱盖房子、娶媳妇,把自己给耽误了……
“你是谁?”四真看着这个人有点面熟,记不清在哪儿见过。
木说他跟雄一个班,是放炮工,和雄是多年的老伙计,说了自己的名字。
四真想起这个人是谁了,眼睛转了一下,笑笑。
木说:“你嫁给雄,不只是嫁给雄一个人……意思你明白吧?”
四真表示她早就明白了,要木不必绕弯子,有话直说,“不就是没嫁给你吗!没关系的。”她在床沿中间坐着,往床头挪了挪,给木腾了块地方。不见木上床,她问:“你从来没‘玩’过吗?”
木说:“嫂子,你太过分了。你是作践自己,还是作践我们挖煤的?”木的脸些黑,目光冷峻、威严,“实话告诉你,你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很清楚。你不要以为雄软弱好欺,再这样下去,可能有人要管管你们的事儿。”
四真说:“哼,你算老几!”
“你别管我算老几,反正我把话跟你说到了,你要是不把我的话当话,恐怕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”
“你要怎样,你敢杀我?”
木站起来,没说杀不杀她,只彬彬有礼地说:“好,嫂子再见。”带上门走了。
木刚走,四真就把两只高跟鞋接连砸在门上,嚷着:“你敢!你敢!”砸完了门,她就趴在床上哭了。她伤心伤远了。她是在报纸上看到矿长的一篇文章才决定嫁给矿工的。矿长说现在煤矿变化很大,矿工的地位也提高不少,但社会上仍有人对矿工存有偏见,致使煤矿工人找对象难。文章许诺,如果有姑娘愿意把爱情献给矿工,矿上将热烈欢迎,并给予较高的荣誉。她来了,矿长没有食言,矿上对她的欢迎是够隆重的。她和雄举行婚礼那天,小餐厅宴席摆了十几桌,不说矿领导,光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 排行榜
排行榜 最新看点
最新看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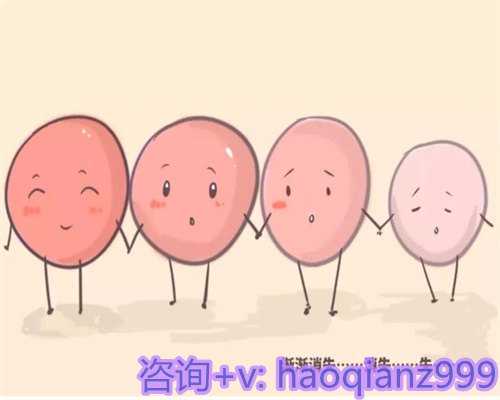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编辑推荐
编辑推荐